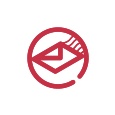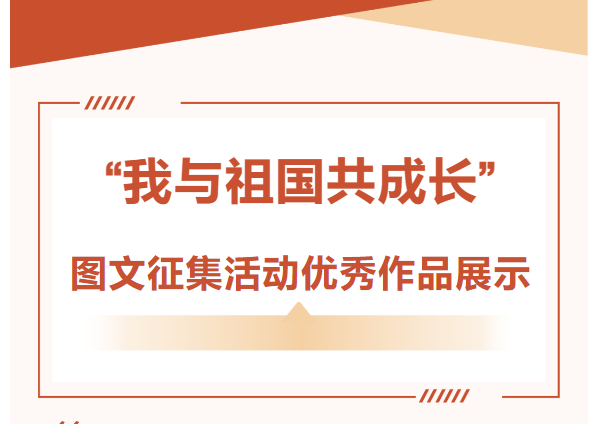
这是一把传承了四代的剃刀,曾祖父初次握起时,刃口映照着煤油灯跳跃的火苗。如今在我掌中,手感依旧温润,仿佛时间从未在它的钢面上留下痕迹。
.jpg)
我们家的理发史,始于1907年。曾祖父在小村庄开了“陈记理发”的小铺子,没有霓虹招牌,只在木板门上用毛笔写着“梳洗洁净,面目一新”。店里摆着老式纯铁烫发棒,每次烫头前,都要在火炉旁反复加热,铁棒子烧得见红,映着客人期待的脸。
祖父十六岁接手铺子,最拿手的是“睡剃”的绝活。客人靠在特制的理发椅上,在热毛巾的蒸汽中昏昏欲睡。祖父的剃刀如毛笔般轻盈,沙沙声中,胡须应声而落,客人竟能安然入梦。他总说:“让人睡着理发,是手上功夫到了家。”

到了父亲这代,发廊开始流行染烫,电动推剪的嗡嗡声取代了旧日宁静。父亲却守着手推剪的韵律,“咔嚓咔嚓”的声响,像老座钟的摆锤般沉稳。他常说:“剪发是修面,更是修心。”许多客人宁愿多走几条街,也要来听这熟悉的声音,在老式转椅上找回片刻从容。
如今,老店由爷爷偶尔照管。他说,守着铺子不为赚钱,只是放不下那些陪伴了一辈子的老物件——磨得发亮的转椅、铜制的刮胡刷,还有那把传了四代的剃刀,更放不下多年如一日来理发的老朋友们。

到了我这一代,虽从小耳濡目染,对老式理发略有了解,却未能潜心学习这门手艺。今年秋天,我踏入了大学的校门,成为一名大一新生。课堂上传授专业技能时,老师反复强调,“手上功夫要精,心里要有数”,竟让我想起祖父磨剃刀时的模样——同样的屏息凝神,同样的精益求精。原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对技艺的敬畏与执着,始终是相通的。
剃刀会老,手艺却能常新。在时光里流转的,何止是四代人的故事。小到一家理发店的百年守望,大到国家民族对传统技艺的守护,都藏着同一份对文化根脉的执着。或许下一个百年,仍会有孩子在这把转椅上完成人生第一次理发,我会告诉他:“理去的是烦恼,留下的是从容。”
这便是我们家的故事——“一把剃刀,四代传承”,剪不断的,是对每一位顾客的尊重和对手艺的敬畏。